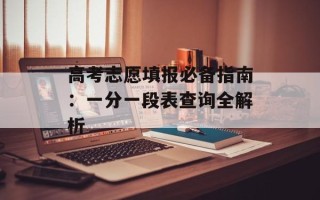文=叶阿七
画=马桶
编者的话
做故事长沙这个公众号以来,很多朋友问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绘画功底,我说基本没有,只是小时候在青少年宫学过两年国画而已。
从那个时候起,就流行让小孩子上各种兴趣班了,书画、音乐、跳舞、奥数等等,说是“兴趣班”,其实大部分小孩子并不是真正的感兴趣。或者,即便真的有兴趣,到了五六年级,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初中,自然也就把这些兴趣荒废掉了。
我就是个典型,一直到三十多快四十岁,又才重新拿起画笔( *** 无奈,自己画 *** 画省钱)。
最近看到新闻,说正在拆除重建的长沙市青少年宫大概10月份就可以重新 *** 了。
那么我们来怀一下旧吧,今天是一个又漂亮又有才的长沙妹子写的文章,回忆自己小时候在青少年宫学画的往事,非常有趣,看得我好开心。
老人都说,三岁看大,七岁看老。于是,自从娘老子发现天生猫弹 *** 跳的我唯有画起画来陀螺 *** 不转能一坐两个多小时以后,就认定我是马良再世,不顾出身军人家庭没有半毛钱艺术细胞的我爷(yá,长沙话中指 *** )的反对,在我五岁那年把我送到市青少年宫学画,希望我将来哪怕不是块读书的料,至少也有一技之长能养活自己。保不齐在弥留之际还能留个画家的美名,改良一下我叶家人的艺术基因,光宗耀祖一把。
事实证明,我娘极其有远见,虽然我并没有走上艺术生的道路,但是这些年兜兜转转机缘巧合都没能离开这么个圈子,估计将来也出不去了。
当然,这一切的一切,还要从我梦开始的地方——长沙市青少年宫讲起。
位于中山西路的长沙市青少年宫
青少年宫位于中山路和又一村巷的夹角,旁边有条专卖画具的教育街,扒手特别多。青少年宫正门开在又一村巷,后来我大一些的时候就在中山路上开了个偏门方便 *** 家长接送停车。
自从开了偏门之后,我总是拉着大人从又一村巷绕过正门走偏门进去,我娘问我原因,我不作声。其实是因为青少年宫正门进去几步路就是 *** 院,隔三差五的就放恐怖片,周围高楼也好,小商铺也好,时时刻刻密密麻麻贴着整版墙面的 *** 海报,我从小记 *** 就好,看到恐怖海报会整晚睡不着觉。
后来有一天心情好跟我娘坦白这个事,我娘一脸不屑的骂我作。
那时候青少年宫的绿化做得是真好,里面也没什么特别高大的建筑,住在附近的老口子们经常在里面乘凉散步,有闲心还可以喂喂草坪里的鸽子,带崽捞捞鱼套套圈打打气球;还有好几个露天茶室咖啡馆,小白领周末喜欢来这里约个会办个公,顺便多接触下细伢子,培养培养自己养崽的耐心和爱心。
青少年宫里面有两栋上课的楼, *** 的一栋叫培训楼,专门教美术;靠南的一栋就是活动馆,是小 *** 艺术集团的大本营,里面不仅有办公的,还有计算机、外语、美术、舞蹈、播音主持等等各种培训。
活动馆
最开始,我在培训楼学儿童画,路过活动馆的时候就在想,这栋楼里面怕是有几千百把万 *** ,个个都要在这里交报名费,真是有钱。
有次我画纸用完了,临时跑到活动馆二楼卖画具的小窗口去买,结果 *** 比隔壁教育街翻了两三倍,气得要死,下楼的时候还瞟了一眼招生办公室,心里哇凉哇凉的,唉,以后我要是能搞少儿培训就好了,怕莫是要赚肿。
从五岁开始我就雷打不动风雨无阻的去青少年宫学画。每个礼拜六下午,一下午两节课,两个半小时,中途休息二十分钟。有时候是我爷送我,有时候又是我娘把我送过来。
看到老师正式上课了,他们就到大厅里和别人的爷娘坐在一起扯卵谈,讲讲自己屋里崽上了什么二课堂,聊聊最近工作上老板又何什结筋,扯到没话了就跑到教室门前踮起脚尖,隔着小小的门窗洞看看崽伢子有没有认真画画。
碰到两口子都没事就一起陪我上课,把我对教室里面一甩,就挤进 *** 院门口高举着棉花糖和饮料的长龙中,和小年轻们一起排着队去看 *** 。
后来,中山路红色剧院旁边开了长沙市之一家肯德基,爷娘发工资的那一周就会带我过去吃儿童套餐打个腰餐,吃吃喝喝还有玩具拿,比过年还要开心。每周六下午四点还有肯德基的漂亮姐姐在店门口教跳舞,我出得众,把嘴巴一抹就跑去跳,想方设法的争当小老师,就为了多拿几个奇奇贴纸和荧光卡片,回头向院子里的小伙伴炫耀。
正在重建中的青少年宫 *** 来源:《潇湘晨报》
说回学画往事,班上三十来个人,两人共一个桌子,抽屉比一般的课桌抽屉厚一点,方便放画具,水彩水粉油画棒、宣纸卡纸美工刀、国画版画拼贴画,每个人都是大包小包的来,又大包小包的走,确实是有点麻烦。
绝大多数报班上课的伢子都不是自愿的,大都是被家里左哄右骗撮过来的,正是猫弹 *** 跳的时候,怎么可能老老实实上这么久的课,把 *** 都坐穿?妹子倒还好,基本上自己还是有点兴趣,加上 *** 格也本分些,上课态度认真端正。
于是,班上的妹子和伢子总是水火不容,伢子坐不住,一节课还没完就拿妹子画具抢妹子的画,想方设法的撩人逗乐;妹子又烦又没辙,抢也抢不过,打也打不赢,气急了就哭,只要有妹子一闹起来,课就上不下去,必须中场休息,搞得大家都很烦。
本来座位是先到先得,后来老师只好排了个座位表,把喜欢聚众 *** 的统统支开,自此 *** 。
青少年宫里的雷锋像
我的同桌恰好是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小伙伴,肤色黝黑,牛高马大,人靠谱又土豪,有好些只用一次的画具,我舍不得买就找他借,他有求必应从来没对我甩过脸,沉稳友善得可怕。
他上课也画,课间也画,从来不跟老师走,自己画自己的,不闻不问班里的闲事,不交朋友不聊天,遗世而 *** 。
我不好意思问人家名字,就叫他大侠,他也懒得跟我搭腔,就随口称我女侠。一开始我还怀疑这货搞东搞西装神秘的,画画到底行不行啊,后来交作业才知道,人家一张画撑死画二十分钟,一画一个A+,果然是在下输了。
等到跟他稍微熟络一点,我问能不能看下他的画,他顺手把刚画过的稿子递给我,我仔细看了两眼,觉得似曾相识,像我当时死忠的本土少儿读物《小溪流》A卷里面的画风。我说起这事,他头也没抬,告诉我,那就是他画的。
我瞬间像被电打了一样,任督二脉都通了,鸡皮疙瘩从脚起到了脸上,久久不能平息。
陪伴很多小朋友成长的《小溪流》 ***
大侠的存在简直是我幸福童年生活的一大阴影,每个周六准时准点笼罩在我头顶上空,给原本把画画当作一大乐事的我带来沉重的生存压力。天哪,既生他何生我啊,人和人之间的区别,怎么好像比物种和物种之间的差别还要大!
从那以后,大侠在我心中的形象比起他个人的胚子伟岸了一倍,每当我想咋咋呼呼释放天 *** 或是偷懒 *** 发呆转笔的时候,心中就有一个声音站出来喊应我——要玩就去别的地方玩,不要打扰大侠画画!要是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别个璀璨艺术家之路上的绊脚石,那你就会抱憾终身、死不瞑目、遗臭万年唻!
当然,细伢子就是细伢子,难免有些花花肠子,虽然大侠已经被我奉为精神领袖,但是每次作业讲评我都拒绝把画和他的摆在一起,其实不仅是我,班上根本没有人愿意把画摆在他旁边,相形见绌这个道理自不必教,自尊心这个东西更是人人都有。
于是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发跳不起来了,全都屏息凝神坐等老师亲自排画,暗自祈祷自己不是今天的背时 *** 。
等到我七岁半,儿童画培训班终于玩不出花样结了课,带了我们两年半的那个温柔如诗、人美如画、比亲妈还甜的女老师也终于十月怀胎准备临盆了。
最后一节课上,我跟大侠扯起谈:“你猜洪老师会生个伢子还是妹子?有个长得咯好看、 *** 格又咯好的娘,她屋里崽怕莫也是前世积了德咧,你讲是不是?”
大侠特别不屑的瞄了我一眼,连笔都没有停:“那就不见得唻,我们是给她钱赚的,她崽是要化她口袋里的钱的,你讲她会对哪个态度好些?”
我正摇着椅子 *** ,差点摔个狗 *** ,原以为大侠是个愣头愣脑的画画 *** 才,没想到啊,居然还有这么一手。
所以说,人就是这么捉摸不透,不仅是大侠,我也是。有课上的时候,嫌耽误自己周末出去玩,没课上了,又反倒是心里空落落的,宅在家无所事事。虽说素描更好是从九岁开始学,但我娘怕我在家里闲到发霉,八岁一到就给我报了班。
这一次,为了表明对我的支持和厚望,我爷特意跑到五一路文化用品商店花重金给我买了个有斤把重、相当扎实的四开画夹,那个时候我身高也就一米四几的样子,偶尔没人接送就背画板提画箱自己跑路。影子投在地上只看到一张大板上面伸出半个头,下面两条鸡把子脚步履蹒跚,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格外凄凉,从教室走到公交站十五分钟的路程还带着喘,想想就心酸。
我外婆说细伢子一天一个样,真是没错,素描班里 *** 岁的同学就是和之前五六岁时候不一样,说不清到底是人长大了就懂事了沉静了,还是因为画室窗帘紧闭、白炽灯和写生灯的光亮远不及日光温厚,又或者是教素描的男老师刚从美院毕业尚且有些拘谨,总之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子清冷的距离感。就连像我这样羊五六成的 *** 自觉不多说一句话,生怕惊扰了周边石膏像的午觉。
画累了就去门口削铅笔,顺便呼吸下新鲜空气,又看一眼隔壁儿童画的教室,好生羡慕啊。以前讨厌的油漆笔里香蕉水的味道,似乎都比4B铅芯的气味更加香甜;美工刀在丙烯颜料和画纸之间刮擦的声音,也比炭笔排线条的沙沙声有趣得多。
啊,当时年仅八岁的我,竟然像大人一样,怀起旧来。
画完一年的石膏静物,全班搬到活动馆,开始学钢笔速写。这时候带我们的,是个常德口音大腹便便的男老师,每节课都淘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给我们当画具,今天拿双不知道从哪里捡的九十年代末的滑板鞋,明天又提着个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解放包,有时候图了撇把门口的垃圾桶搬进来就让我们围着画,有时候又极其讲究把家里的唐三彩扛了过来……前前后后画过不下四十种没上过教科书的东西,后来估计是找不到可画的了,干脆抽张椅子坐在教室正中间,理理肚皮处衣服的褶子,翘着个二郎腿让我们画他。
印象中,这个老师 *** 心重, *** 子直,一起上课的有好几个正好小升初,家长想请他开开小灶备战特长生 *** ,他张嘴就说人学习态度如何、天分如何、将来要真走这条路又该如何,全 *** 心人家远大前程去了,一句补习的事都没提。
我在旁边听他们叽叽喳喳,暗暗夸这老师真是业界良心,谁知道人家家长压根不买账,嫌他话太多,最后找了美院的在读 *** 搞家教。
虽然这老师喜欢搞事——比如,叫我们去天心阁写生,结果买了门票坐在城墙边上画外面 *** 的沿街门面;喊我们到烈士公园采风,然后集体踩船上湖中岛去画青山桥——但是打句良心讲,我个人还是挺喜欢他的,毕竟我迟到那么多次他也没在评画的时候给我穿过小鞋,确实是宰相肚里能撑船,表里如一。
青少年宫里的刘胡兰像
计划赶不上变化,还没来得及好好学色彩,学校就给我们五六年级的人安排了小升初集训,我礼拜六的美术课自然要向正课低头。于是,我的马良之梦在十一岁那一年含恨夭折,被淡忘在了基础教育的重压之下。
值得庆幸的是,生活的维度向四面八方蔓延,我不只有画画这么个兴趣,也不只有青少年宫这个地方承载着我的童年时光,但是只要一想到与之相关的一切:门口的章鱼小丸子、正门对面的无骨鸡柳和又一村的春卷、公交站旁边小推车里的烤红薯、不远处台北豆浆的红豆汤圆,还有中山路和建湘路交角处的射手座美少女 *** 等等等等,缺一不可又独一无二的拼凑成我一生一次的童年,便感到无比宽慰。
前几天路过先锋厅,看到新修的青少年宫洋不洋土不土,好像比中山亭还要高,也不知道里面雷锋和刘胡兰的雕像还在不在,被护栏圈着的四方草坪还在不在,正门大道上的两排彩旗还在不在。
当然,在这个见证着成长的地方,物质的变迁显得无足轻重,唯一永恒的,便是藏匿在灌堂风里,只属于这一方人的无数个春夏与秋冬。

作者简介:叶阿七,90后,湖大建筑学在读研究生,怕死不怕红的十八线设计诗、画家、戏剧编导、乐团指挥,本土文艺圈中一枚正在茁壮成长的万金油。